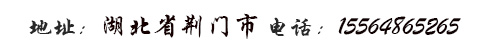小说连载作者一勤江山六
|
江山河北一勤城墙上下、四处点起了火把,陈如呆坐在角落,木然望着。几个*士把剩下的木头点起一个篝火,篝火辉映下,照见了坐在墙边的张荆。只见他抱着刀坐着,很沉默,像是有许多心事。马迁和王鲁坐在不远处的火把旁,他俩看向张荆小声议论着。马迁悄声说:“那家伙功夫可够厉害的,白天砍了不下一百颗人头吧!”王鲁也望过去,说:“可不,那一刀刀砍的,真解恨!”“你听说他的事儿了吗?”“啥事?”“他一个人把他全家几十口都砍了头!”“啊?为什么?”“具体不清楚。”王鲁望着张荆,说:“我算是小巫见大巫了,可真够心狠手辣的!”“我还是离他远点儿,省得他一个不高兴,把我给劈了!”马迁一本正经地说。“不至于吧?”“那可说不好。”马迁想到什么,叹一口气。“叹啥气啊?”马迁笑一声说:“我本来以为死定了,没想到又让耿大人给弄出来了,这世道太荒谬了!”“你犯了什么事?”“偷东西。”马迁无奈地摇摇头。“你偷了啥宝贝,给你判死罪?”“要不说嘛。”马迁表情深沉了,跟他说起来。洛阳。一天夜里,马迁身着一袭夜行衣,快步走在街道上。他边走拿一块黑布蒙上面,悄然翻进路边一家高门大户。夜色中,远远传来打更人敲打棒槌的声音。昏暗中,马迁摸到一个房间外,拿一根铁丝打开门上的锁,推门而入。很快便出来了,身上系着一个黑布包,又翻上墙头,正要跳下去,脚下一滑,瞪着眼一头摔趴在地。他赶紧爬起来,一瘸一拐地跑远了,身后还响着棒槌的敲打声。王鲁好奇地问:“你把传国玉玺偷了,还是咋的?”“哪啊,就是些珠宝。”“就凭这就判死罪?”“你听我说啊。”一天夜里,马迁正在睡觉,一伙官兵突然进屋,将他擒住按在地上。只片时,官兵便在他床底下的箱子里搜出了珠宝。“估计有人见我花钱手大,把我告了。”马迁被押到大堂上,跪在地上,低着头,眼睛左右溜看。太守厉声呵斥:“小贼,如实招来!”两边的衙役把手中的杀威棒连敲三下,马迁眼睛滴溜片时,抬起头来。“大堂上我心想,还是别等动刑具了,老实招了得了,无非是杖罚,顶多是发配,就如实说是偷了哪个大官的。你猜怎么着?我这一如实招供,反而出事儿了!”太守脸色变得凝重了,他起身思索片时,瞪向马迁,一声呵斥:“大胆毛贼!”王鲁问:“咋了?”“因为我偷的那个大官是个有名的清官,家里有这么多珠宝,那还说得清?再加上那大官眼看又要升官,如果这事儿宣扬出去,对他肯定不利!”“哦,原来这样。”“那审我的太守和那大官是一系的,官官相护,那太守随便给我加了些罪名,就这么问了死罪。”“你可够倒霉的!”“你说这是啥世道?我说了一辈子谎,好不容易说句实话,却要被处死!”王鲁笑得也有些无奈。“可没想到,后来又被校尉大人给弄出来了,唉!”“算你小子命大!”沉默片时,马迁看着王鲁问:“你犯了啥事?”王鲁避开马迁的目光,说:“没啥,没啥。”城墙上又点起几个火把,他俩望过去。城墙上,耿恭和那老人注视着城外匈奴兵的动静,匈奴的营盘里闪着繁星似的密集的火光。老人望着说:“匈奴擅长骑射,不擅长攻城,况且此时正值暑夏,我们占尽了天时、地利,我料定他们攻不进来。看他们火把的队型,他们明天一早准会再次攻城,万不可掉以轻心!到时不要心急,等他们冲上来再放箭!”耿恭听了点点头。耿恭沉默片时,望着老人试探地问:“前辈箭法了得,不知何时来的西域?”老人望着远天,说:“算一算,我到西域快六十年了!”“前辈也曾从*吗?”老人沉默片时,说:“过去的事就不提了。”说完他转身下了城墙,走在街道上,渐渐没入夜色。耿恭望着老人走远,自言自语地说:“六十年前,不就是前朝元帝晚年?他对兵法的纯熟远在我之上,对西域又如此了如指掌,难道他是元帝所遣进兵西域的将*?他箭法了得!陈将*?不可能,陈将*早已战死,且死后封侯!怎么可能?”耿恭望着眼前的孤城,一轮皎洁的明月静静地升在山际之上。天亮后,匈奴再次大举攻城,依然用云梯强攻,不同的是攻城的匈奴兵都拿了一面藤甲盾。藤甲盾确实能抵挡滚石、檑木,而强劲的弓弩能穿透藤甲,依然能压制匈奴兵。王鲁往下抛着滚石、檑木,边抛边骂:“别以为躲在个鸟盾牌后面就没事儿,大爷我照样砸扁!”王鲁又抛下一个滚石,直接将城下一个持盾的匈奴兵,连盾带人砸扁在地,他大笑着。正这时,飞来一支箭,射在王鲁左肩。他疼得弓着腰,右手掰断箭杆,脸上一阵怒色,弯腰又拉上一个滚石。他面前的云梯爬上了一队匈奴兵,他大喝一声将滚石抛下去,直接砸落一串。“来啊,孙子们!”马迁依然使一支长矛,匈奴兵有了盾牌,他连连刺杀不中。张荆还使单刀,对着爬上来的匈奴兵,一刀砍下去,将盾牌砍出个大豁口,豁口处溅上一片血迹,匈奴兵应声滚落。老人把手中的弓,瞅准空当,一支支箭射出,撂倒一个个攻上来的匈奴兵。耿恭站在城墙上,看着攻势如潮的匈奴兵,镇定地说:“换箭!”城墙下放着一个大锅,锅里是老人熬制的草乌,*士们把一捆捆箭沾在锅里,往城墙上扛。弓箭手都换上了*箭,被射中的匈奴兵,片时便倒地吐血而亡。攻上来的匈奴兵见状,面露惊惧,连连后撤。如此一阵还击,进攻的匈奴兵纷纷退了回去。远外,攻城的队形依然齐整。匈奴中*王旗一挥,又一波匈奴兵汹涌着冲杀上前。同时攻上来一队匈奴兵,用藤甲盾遮盖着,推着一辆装有粗大撞城木的推车,很快来到城门前,一声声震天响地撞击城门。弓箭手接连朝攻城门的匈奴放箭。耿恭朝城内挥手,一队*士拎着盛有热油的木桶快步走上来。耿恭指着城门前:“倒!”汉兵一起将手中的木桶倾倒,里面粘稠、滚烫的脂油一股脑地浇下去,底下的匈奴兵被烫地捂着脸哀嚎起来。“放箭!”耿恭一声令下,城墙上射下一支支火箭,城门前粗大的撞城木、推车以及藤甲盾纷纷起火,连同匈奴兵身上也着了火。被烧着的匈奴兵,一个个丢盔弃甲、仓惶逃蹿,片时全被射中,倒地身亡……匈奴再次退兵。城墙上的*士们喘着气,一个个静静地望着,好久没人说话。夜里,城外走来一个黑影,渐渐走近。城上*士拉着弓,厉声道:“城下何人,报上名来!”城下人扬声说:“我乃车师国使者!”守门的*士打开城门,一个气质不俗的年轻人走进来。路两边的火把闪烁着,两个*士带使者进城。城中一个还算典雅的民房,是耿恭的议事之处,*士带使者走进院子,来到堂屋外。“禀报校尉,车师国使者求见!”片时,屋里传来回答:“进来。”使者走进屋,耿恭上下打量他片时,朝身旁的椅子摆手说:“坐。”使者坐于下首。“不知所来何事?”“王妃派我来问,不知校尉大人可有需求?”耿恭看使者一眼,问:“王妃派你来的?”使者点点头。耿恭思考片时,说:“那请你转告王妃,什么也不缺!”说完耿恭站了起来,背对着使者说:“送客。”一个*士走进来。使者正犹豫间,耿恭背对着他说:“也代我谢过王妃,毕竟正在交战,以后不要再来了。”使者起身鞠一躬,转身出屋。耿恭望着屋外车师国的方向,又回想起王妃那次相送的情景。两人在戈壁上纵马奔驰,王妃笑声连连。风吹落了王妃头上的簪子,她的长发在风中飘舞,耿恭看得出了神。骑了一段后,两人并排着缓步前行。风总是吹乱王妃的头发,耿恭于是从马鞭上扯下一根皮绳,递给王妃。王妃会意,朝耿恭笑笑,接过皮绳,系好头发。王妃看着前面说:“其实我并不是什么公主,不过是个侍女,来到大漠,跟坐牢似的。”“你来这里多久了?”“都十年了,十年啊,我怎么过来的!当初,我刚和亲远嫁到车师国不久,匈奴就趁中原大乱之机,大举进攻西域各国,杀了倾向中原的车师国国王,扶植了亲匈奴的国王的弟弟安国上位……”安国登基当天便迎娶了王纪。当晚,王妃一身异域新娘的打扮,一脸冰冷地坐在床头。安国一身新郎装扮走进来,脸上带着酒意。安国走上前,单腿跪在王妃跟前,说:“王妃,婉儿,你刚来车师国的时候,我就喜欢上了你……”王妃依然端坐着。安国脱了王妃的鞋子,亲吻着她的脚说:“婉儿,为了能得到你,我想尽了办法,相思害得我好苦!”王妃只是漠然坐在床头,安国亲吻着她,将她按倒在床上,解开她的衣裳……王妃眼角冰冷的泪水滴落。王妃和耿恭骑马走着,远远地看到了金蒲城。王妃拉起缰绳,说:“就送到这儿吧。”她掉转马头,又拉着缰绳回头说:“有缘再会,驾!”说完骑马走了,耿恭一直目送,直到王妃的背影隐没在*沙中。(未完待续) 作者简介: 原名孙大勇,曾获22届、25届汉新文学奖(美国),文华杯全国短篇小说大赛三等奖(中国小说学会举办)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囚笼》,出版小说:《鼠盗船:夺宝之战》,长篇小说《十七岁的情人》(原名古蛇)连载于“国际日报”,在国内外报刊杂志发表多部中、短篇小说,作品入选多部选集。 征稿 《新疆文学》是一个以主流和先锋文学为导向的 |
转载请注明地址:http://www.caowua.com/cwrybw/7433.html
- 上一篇文章: 人参蛇山峰什么都拿来泡酒
- 下一篇文章: 平肝息风中草药地龙